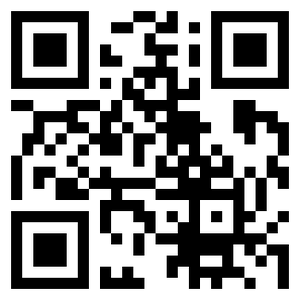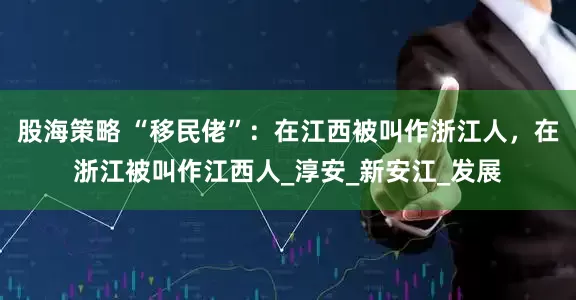
1959年,新安江水电站大坝的合拢,淹没了淳安大部分土地,迫使30万淳安人离开祖辈相传的家园,开启了漫长的迁徙旅程。我的父亲便是其中一位,当时他年仅三岁,还是被爷爷用簸箕挑着一路背过来的。我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桃溪乡徐家村苍坑自然村,因此我是地道的江西新干人。直到20岁之前股海策略,我从未踏足过浙江,更谈不上亲自走访淳安。对淳安的记忆,只能通过长辈们的断断续续的叙述了解。然而,在我的户口薄上,籍贯一栏却清楚地写着浙江省淳安县。这一字一句无形地提醒着我,我与那遥远的淳安有着复杂而深厚的联系。
多年来,我一直有一个愿望,就是通过文字记录下淳安移民的历史和发展轨迹。我希望将这段独特的历史留下,尤其是在村里的老年人陆续离世后,这种责任感愈加沉重。尽管一直未能静下心来专心写作,工作繁忙之下只能零零散散地写些片段,目前,我在自己的专栏“移民佬”中已经发布了三十多篇文章。如果您感兴趣,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“莽子说”。话题转回正题,继续深入探讨。
展开剩余61%事实上,淳安(新安江)移民及其后代内心深处,始终保存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感。这种情结,如同一道深深的伤疤,时常在某些特定的瞬间,无声无息地被触动,甚至在不经意间被揭开,带来一种痛苦的回忆。尤其对于亲身经历过迁徙的那一代人来说,这种情感更是切肤之痛。长辈们常提起:“父亲砍断了陪伴母亲多年的那口锅,母亲悲伤地跪在灶前久久未起;或者在漫长的迁移途中,某个亲人因病离世,眼睁睁看着他与世长辞……”这些悲伤的故事,常常深藏心底,很多时候,移民们连提起的勇气都没有,他们宁愿选择沉默和遗忘。
浙江人勤劳、坚韧的性格,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,是众所周知的。在搬迁至江西的这些新安江移民,通过多年的艰苦努力,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已经不亚于当地的江西人。江西作为一个包容而慷慨的省份,江西人民的热情与善良,也在移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然而,尽管如此,移民们依然无法忘记他们远在浙江的故乡。
尤其是进入90年代,浙江的经济高速发展,成为全国富裕的典范,淳安的经济和城镇化建设也因此发生了显著变化。这种发展,使得部分新安江移民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平衡感和疑问:“千岛湖发展得如此迅速,村民每年都能分红,如果我们没有迁走,今天的千岛湖怎会有如此的发展?我们为千岛湖付出了那么多,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与此相匹配的回报?”这类想法听上去似乎合乎逻辑,但实际上,在新安江移民迁往江西之前,淳安的每个村子都选派了代表去江西考察,回来的代表普遍对江西表示认同。因此,很多移民本着“去江西就能安稳生活,能有饭吃,能有柴烧”的美好愿景,才选择了自愿迁移。
因此,一味渲染新安江移民的悲情,并非完全公正。更何况,尽管移民们的心依然向着千岛湖,现实是,千岛湖早已不再属于“移民佬”们。这个事实已经不可更改,也不容忽视。
随着岁月流转,某些东西终究无法长久保持,如新安江移民心中的“浙江情结”,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。就像我的父亲,由于与舅公(父亲的舅舅)、姨奶奶(父亲的姨妈)等亲戚的深厚感情,父亲对淳安怀有很深的情感。然而,我作为在江西出生的孩子,对父辈的浙江情结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共鸣。新安江移民曾经的痛苦和泪水股海策略,终将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沉淀,成为永恒的记忆,而不是社会矛盾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的后代必定会与江西本地人融为一体,成为同胞,不再有任何隔阂。
发布于:天津市振兴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